苏轼被贬读后感(汇总6篇)
ID:4311507
时间:2023-10-07 13:52:43
上传者:JQ文豪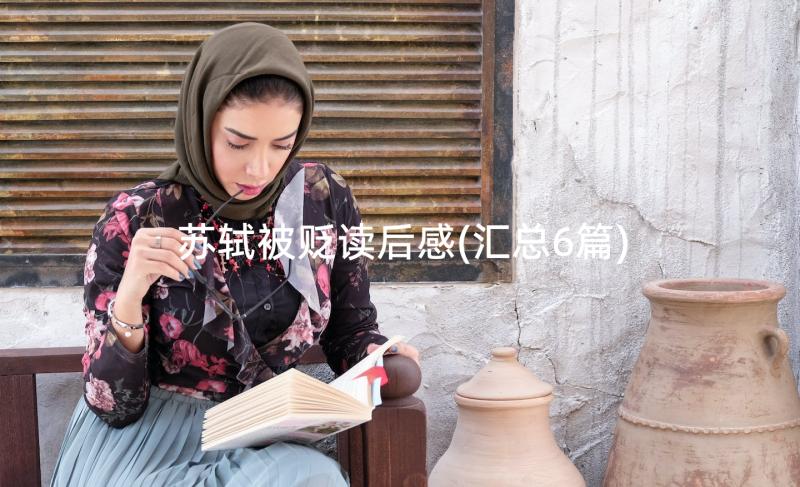
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,这样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。读后感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,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读后感呢?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,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。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一
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。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,任职多地;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,互生互补。说简单是因为,读其生平与作品,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,即一个元气淋漓,思想与情感丰富,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。
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,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,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。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,苏轼是45到49岁,正处壮年,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,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,酝酿出前后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。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,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。虽然乌台诗案中,苏子被“顷刻之间,拉一太守,如驱犬鸡”,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,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,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。
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……(《赤壁赋》)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(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)
这样的旷达,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。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。
但我这次读其传记,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。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,而更了些逸气。不仅行文自然巧妙,文本天成,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;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,发人深省。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:“大凡为文,当使气象峥嵘,五色绚烂,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”(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)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“气象峥嵘,五色绚烂”,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“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”了,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。孙过庭论书道:“初学分布,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,务追险绝;既能险绝,复归平正。”学书如此,其实为文也这样,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,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。
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。
元祐八年(1093),苏轼,身至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,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,正是“冠盖满京华”的时期。然而高太后去世,政坛巨变,于是绍圣元年(1094),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(英州),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,最终贬到惠州。
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,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,身边只有小儿苏过,和侍妾朝云。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,其心境可想而知,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。
贬往惠州路上,过大庾岭时,他写道:
一念失垢污,身心洞清净。
浩然天地间,惟我独也正。
今日岭上行,身世永相忘。
仙人抚我顶,结发受长生。
没有悲伤,没有哀怨,一切的辱与荣,垢与净,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,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,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,助其修道成功。
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:
我本修行人,三世积精练。中间一念失,受此百年谴。
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,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,误落尘网中,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。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。
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:
仿佛曾游岂梦中,欣然鸡犬识新丰。
这难道是梦中吗?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。这真是太富禅机了,《红楼梦》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,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。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,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,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。
东坡惠州的诗文,正是借助佛老思想,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:
譬如原是惠州秀才,累举不第,有何不可!(《与程正辅提刑》)
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,却在一个小村院子,折足铛中,罨糙米饭便吃,便过一生也得。(《与参寥书》)
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,自然天成,臻于化境。随意的一篇游记,给人无限启迪:
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,纵步松风亭下。足力疲乏,思欲就亭止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,意谓是如何得到?良久,忽曰: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?”由是如挂钩之鱼,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,虽兵阵相接,鼓声如雷霆,进则死敌,退则死法,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。(《记游松风亭》)
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,流光溢彩,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;而是一任天成,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。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,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:
绍圣元年十月二日,轼始至惠州,寓居嘉佑寺松风亭。杖屦所及,鸡犬皆相识。明年三月,迁于合江之行馆。得江楼廓彻之观,而失幽深窈窕之趣,未见所欣戚也。岭南岭北,亦何异此?(《题嘉祐寺壁》)
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,一处有一处的妙处,一处有一处的局限,这样看来,便可随遇而安了。
果然,稍后来到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”的儋州,他也能怡然处之。此时,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,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:
始至南海,环视天水无际,凄然伤之曰:“何时得出此岛耶?”已而思之,天地在积水中,九州在大瀛海中,中国在少海中,有生孰不在岛者?覆盆水于地,芥浮于水,蚁附于芥,茫然不知所济。少焉水涸,蚁即径去。见其类,出涕曰:“几不复与子相见。”岂知俯仰之间,有方轨八达之路乎?念此可以一笑。
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,如此观之,一切便可释然了。这种文字置于《庄子》三十三篇中,也别无二致了。
谪居儋州之际,朝云已经去世,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,积蓄已基本花光,而自然环境险恶。而这位精神的富翁,却能用自己的达观,将如此贬谪之地,变为乐土。并写出《谪居三适》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。
兹录其一:
旦起理发
安眠海自运,浩浩潮黄宫。
日出露未晞,郁郁蒙霜松。
老栉从我久,齿疏含清风。
一洗耳目明,习习万窍通。
少年苦嗜睡,朝谒常匆匆。
爬搔未云足,已困冠巾重。
何异服辕马,沙尘满风鬃。
琱鞍响珂月,实与杻械同。
解放不可期,枯柳岂易逢。
谁能书此乐,献与腰金翁。
早起梳头百下,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,以此养生能“一洗耳目明,习习万窍通”。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,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。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东坡居士,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,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。于是他感叹,年少时嗜睡,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,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,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。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,都是满头风尘,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,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。
至此,苏轼还是那个苏轼。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,变为睿智通脱;由流光溢彩,变为平淡冲和;由辞采华茂,变为浑然天成了。(耿世涛)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二
书还没看完,慢悠悠的翻着。林语堂这本书原是用英文写的,张振玉译笔还算不错,但粗糙之处也随处可见,比如卷一第一章处:
一天,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:“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,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,我笔皆可畅达之。我自谓人生之乐,未有过于此者也。”这段文字殊为怪异,而后在网上搜索出一篇天涯高手的文章,才知道原文应为:“某生平无快意事,惟作文章,意之所到,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,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”。
还有一处bug连那位天涯高手也未提到,卷二第七章埋伏笔,“中岳嵩山崩陷”,到第九章呼应,已变成“南岳华山山崩”。此两处究竟是何处出错,是翻译错还是原稿错,抑或是校对错,恐怕需要找英文原版来查了。但是“南岳华山”本身就是个错误,华山好像从来不曾被称为“南岳”过吧。
且丢开这些小破绽不说。
苏东坡的盛名传播了将近一千年,时人称道,后人敬仰,一方面是因他天纵其才,在诗,文,字,画各个领域都出类拔萃;另一方面,他的人格魅力,政治立场,哲学修养也极其贴合中国人的理想。为这么一个完人做传显然不太讨巧,再加上史料丰富评论一边倒,这本传记的“新意欠奉”也在情理中。林语堂在序言中说,“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,正因我了解他,我了解他,是正因我喜爱他。”既然在苏轼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生观,偏爱之心更不加掩饰。
卷二写苏东坡壮年经历,与王安石的纠葛占了好长篇幅,在“王安石变法”和“拗相公”两节,王安石是主角,苏东坡反而成了小配角,这两个章节似乎游离在全书之外。林语堂贬低王安石,我看目的倒不是为抬高苏轼,更多是他想表达对历史的看法。包括对司马光的褒扬也是如此。历史其实无所谓真相,政治也很难分辨清浊,好比一面镜子,每个人照去都是不一样的面目。这一部分能够跟柏杨的书比照着看,那是两种完全相左的意见。跟苏轼不一样,王安石从来都充满争议,历史上是这样,到这天还是这样。
林语堂自己也是个争议人物,但是他的才情倒还算公认的。这本苏东坡传,时不时也有沁人心脾的妙语出现。比如正看到卷三第16章就有这么一句:
倘若哲学有何用处,就是能使人自我嘲笑。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三
今年寒假,奉老师之命买了厚厚一本林语堂的《苏轼传》。本是是想草草读完草草了事,没想到自己却被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所深深震撼,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无限的敬意。
首先,林先生在文中向我们先介绍了东坡的家世,对他影响比较大的应该是他的母亲程氏,他小时读完《范滂传》,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,问道:“妈,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,您愿不愿意?”母亲回答道:“你若能做范滂,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?”。他母亲从小就给他进行好的道德熏陶,也是以后成长成才的一大要素。
接着介绍了他的学习经历,他从小就展露出他的超于常人的才气,但这一点也没妨碍他的努力。苏东坡读书时就将经史诗文、经典古籍都背的滚瓜烂熟,这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,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,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,他决不会毫无头绪。苏东坡的学习经历也告诉我们天才也需要勤奋学习,也需要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。
在《苏东坡传》里不只是介绍了苏东坡其人还介绍了与他最相关的三苏其他两人,他的父亲苏洵,弟弟苏辙。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,气质谨严,思想独立,性格古怪,自然不是与人易于相处的人。再一个就是弟弟苏辙,苏辙的性格与他哥哥不太一样,他的性格是恬静冷淡,稳健而实际,因此也比他哥哥在官场上得意些。写完三苏,又要说说苏轼的妻子,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务实际、明利害方面,似乎远胜过丈夫,所以苏东坡则事事多听从妻子,她是一个妻子,也更像一个聪明的管家,睿智的伴侣。不幸的事她英年早逝,这让苏东坡很是难过,曾专门写过一个词纪念她,这就是与贺铸的悼亡词并称为悼亡词双绝。文中给我们重点介绍了东坡在官场的几次沉浮。苏东坡,他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.改革措施,也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,而是主张稳健行事,凡事皆从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际效果出发,不去阿附迎合,不为“新法”或“旧制”所囿,因而在新旧两党间均受排斥,仕途生涯十分坎坷。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之中,但是他却风光霁月,高高超越于蝇营狗苟的政治勾当之上。他不伎不求,随时随地吟诗作赋,批评臧否,纯然表达心之所感,至于会招致何等后果,与自己有何利害,则一概置之度外了。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,可从他的诗篇,他的文章,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,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、是积极向上的。幽默的他在与王安石谈及王之所谓“字源学”时,引用《诗经》中“鸣鸠在桑,其子七兮”,并父母共九只鸟,以王安石的方式来向其解释为何“鸠”为“九”、“鸟”二字合成,实为嘲讽。即使在被贬至缺医少药的海南之后,对朋友僧人参寥的关心,他仍在回信中说“但若无医药,京师国医手里,死汉尤多。”以此来告知朋友不必担忧。
热爱生活的他仅在美食方面,就有许多轶事。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、自己酿酒,更是传给后世“东坡肉”、“东坡壶”等。他在诗词中,也多次提及美食——“无竹令人俗,无肉使人瘦,不俗又不瘦,竹笋焖猪肉”、“长江绕郭知鱼美,好竹连山觉笋香”、“蒌蒿满地芦芽短,正是河豚欲上时”、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等等,不一而足。
多愁善感的他在《江城子》一词中,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,对其亡妻寄以情思,与其“大江东去”风格迥异,凄婉哀伤。在朝云因瘟疫早逝后,他在《朝云墓志铭》和《悼朝云》一诗中,均表达了深切情爱与伤痛,后来更在《西江月·梅花》一词中,以梅花象征朝云,既似写花,又似写人。
正直的他尽管有过数次因诗而被捕、受审,但仍然不改犀利词风。好友刘恕罢官出京时,他写诗讽刺“群乌未可辨雌雄”,后又写“犹诵麦青青”,对官场荣耀表示鄙夷之意。在某次刚刚被释出狱后,即写诗两首,随后自己也掷笔笑道“我真是不可救药!”
苏东坡异常坎坷的一生,也是豁达乐观的一生。他那种身处逆境却始终保持“成固欣然,败亦可喜”的超然达观,像他的诗词文章一样千载有余情!经万古流不尽!如林语堂先生所言,苏东坡“像一阵清风过了一生”,“根本是他本性的自然流露”,“他的肉体虽然会死,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,则可成为天空的星、地上的河”。让我们仅此感怀东坡居士这位旷古奇才吧!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四
我读《苏轼传》,觉得全书对苏轼的评价,大体与《苏东坡传》相似,林氏的概括即所谓:“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,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,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,是散文作家”,等等。《苏轼传》大体是以这种评价展开的。不过书的副题《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》又表明作者们是极力从苏轼生活经历来理解和描写他的。因此这书自有它的不容忽视的特点。
一、它严格按编年叙事,而且强调苏轼作为作家的一个方面。
全书将苏轼的诗词文章贯穿它的一生,对比看起来,《苏东坡传》就不是这样,它要照顾英美读者的理解力和趣味,诗文不能多引;它使用的传说故事更多,也占更重要的位置。因此,这本《苏轼传》对读者从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了解他的生平,是更有益的。在叙事中展开对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阐释,而且阐释得极好。在此,就表现出王水照先生对苏轼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研究的功底非凡,在传记里应用随心自如。苏轼的心事、文思,与天下的政事,交织一起,所以合了“在苦难中的超越”,而且是一位“智者”的超越。没读过苏集的读者,从《传》中引用的大量诗、词、文中,特别是从并不常见的随笔、短笺中,能领略的,真是不少。
二、林语堂酷爱苏东坡。
林写的是文学性更强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,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散文创作。当然林氏有他充分的历史材料证明,而我总觉其着眼点在于苏东坡的人格,而且是作者喜爱的人格。而《苏轼传》则更带有学术性。它更全面,更讲究论证。的确,苏轼的风流潇洒,几乎是天成。但是,环境也造就它。不论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看生平,还是从生平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,都不单有潇洒风流,而且有个人的痛苦和人民的苦难。乌台诗案中国最可笑的文字狱之一后被贬黄州,是苏轼生活的关键一步。在林、王二传中,都重点写。余秋雨重要散文《苏东坡突围》也选这一段来写。苏轼的人生和他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,在此都是一个高峰。对这一段生活,《苏轼传》无疑写得更丰富。它把痛苦和苦难展示得更充分,以至于惊心动魄。苦难充分,“超越”才有力。林氏过分地渲染了苏东坡在苦难中的乐天、快活,甚至把他在“乌台诗案”里受审时的屈辱与痛苦也说成“有趣”。《苏轼传》则把黄州生活写得更令人可信。比如当时苏轼在许多信里反复叮嘱友人“看讫,火之”,“传闻京师,非细事也”。他是惊弓之鸟了。他在黄州又看到生平所未见的民间疾苦,苦日子也尝到。在此有一点不可不提。苏轼在黄州时写过许多信,其中有一封是给他的朋友也是政敌章忄享的信中对已往表示悔过。林传说,是“一封非常贴切的回信,悔过之意,溢于言表”,是“再得体不过”,简直可请皇帝过目;言外之意是应付,巧于周旋而已。而王著则以为“可能夹杂着个人求助的'动机”。我以为写得较真。王著此是全面反对新法了。这似乎顺理成章。王著写出的诗人,更复杂、真实些。
三、关于王安石变法,林氏的否定也许太简单化。
而王著则更客观些。关于苏、王二人,当然都是大作家,苏比王高。此书提到变法时,曾对比苏、王的见解说:“无论是思想的高度,还是目光的远大,苏轼都无法与一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”。这也是客观的。此书在王安石身上着墨不少,而且是从王安石与苏轼的交往中写的,重头文章在王安石罢相以后。苏轼在金陵访王,政敌又成文友,旧怀尽释,论文极乐。那一大段就写出北宋文人的大度风雅,更写出两位大作家的可爱。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五
平凡的人对于“光芒夜半惊鬼神”的天才总是有种不可名状的畏惧,如徐渭、如梵高。但对于性情平易近人,骨子里流淌着温和谦恭血液的天才,则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喜爱和亲切感,比如苏东坡。
苏东坡是朴实的中国百姓脑海里一切美好形象的真切合体。他实实在在就那么人人眼、他轻轻松松就能够暖人心。他满足了我们对中国文人的所有幻想。
顶着一副粗犷老农的外表,不是不英俊,而是让人看得太舒服。一脉浩然之气用尽,不只为自己,还将那福音传给大江南北的百姓。一声“如蝇在食,吐之方快”,可见他清狂而非轻狂。一叹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可知他用情之真思念之深。
喜爱苏东坡,是因为他在那苍茫天地之间如同一株小草——在奋力钻出黑暗的夹缝之后、在见到惨淡天光的那一刻,以不比常人的坚定之心相信光明,从此长成一棵参天大树。郁郁葱葱,屹立不倒。沧桑笔直的树干是他的独善其身,伸展而开的绿冠是他的兼济天下。几十年人生跌宕,风风雨雨使得他从肉体到心灵,都变成一个不能被轻易伤害击败的人。中国文人敏感脆弱的灵魂,在他这里去掉了多愁与伤怀、抑郁和不安,只留下一种叫“看得开”的心情,叫“想得明白”的心境,和“同情弱者”的心怀。
走近苏东坡,从他那一句“吾上可陪玉皇大帝,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。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”开始。这种生活不同于陶潜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清净,也没有刘禹锡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那么“高水平”。
苏东坡是和谁都玩得来。他可与三教九流为伍,并且从不失那颗赤子之心。这不仅是一种本领、一种生活,更是一种活法!在他眼里,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;在他心底,一涓宽容之泉早就将政敌带给他的不愉快全部带走。因为知爱,因为懂爱,更因为有爱,他成为古今士大夫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。这种活法是他受人欢迎的原因,是他心灵幸福的秘诀,也是他留给这略显苍白的人间巨大的精神财富。
感悟苏东坡,从他那一句“浩然之气,不依形而立,不恃力而行,不待生而存,不随死而亡矣”开始。一个人能对浩然之气有如此深切之感,想必该精神必定贯穿他人生始末。苏东坡正是如此。从朝廷上的当仁不让,到贬谪为地方官的身体力行。他的奏章、他的功绩无一不透露着那不谋私利,一心为民的感情。身在名利场中,诸多不由己。却因为有那股浩然之气,他把决心下得更彻底,他把脊梁挺得更硬。他像一股旋即有力的清风,吹散了所到之处的污浊之气。
想起苏东坡,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个大腹微便便,体态微宽的形象,让人安心让人贴心。他身上没有“文人相轻”的酸味,他身上只有温温暖暖的阳光的味道。时常忍不住在心底唤一句“老东坡”,因为羡慕,因为喜爱,更因为感叹。羡慕他的才华横溢,外加那一副好心肠好脾气。喜爱他儒者的翩翩风度,那是一个翰林大人美好的形象。也更感叹那一颗赤子之心、一身浩然正气、一片坦然心境。
时光早已涤荡了苏东坡心中那因贬谪、因颠簸、因月光、因夜风而生发出的一切忧忧愁愁不达不快,只留下一个摆脱了官场的羁绊、人事的纠纷的大文学家的形象,由宣纸上的墨迹、石碑上的刻纹穿越千古传递到我们面前。翻开旧书,在那无数豪情四射的诗词笔墨之间,我只看见我那温温暖暖的老东坡,带着他的大黑狗,拄着一根竹杖,悠悠然然地行走在世间。
苏轼被贬读后感篇六
东坡的一生极复杂又既简单。说复杂指其仕途上几番沉浮,任职多地;思想上儒释道兼而有之,互生互补。说简单是因为,读其生平与作品,苏轼给你的感觉始终如一,即一个元气淋漓,思想与情感丰富,才华横溢而能永葆赤子之心的真人。
关于苏子的文章多矣,这些文章大都关注乌台诗案后,苏轼被贬黄州几年的生平和诗文。此时是元丰三年到元丰七年,苏轼是45到49岁,正处壮年,处于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成熟期,仕途的坎坷造成思想情感的波澜起伏,酝酿出前后《赤壁赋》和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这样彪炳千古的华章。读这一时期的诗文时,你能感受到一种属于壮年的气息。虽然乌台诗案中,苏子被“顷刻之间,拉一太守,如驱犬鸡”,在囚禁了整整130后贬到黄州任一闲置,但我们仍能从其作品中读出一种浩然之气,这种豪气是只属于这一阶段的。
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。浩浩乎如冯虚御风,而不知其所止;飘飘乎如遗世独立,羽化而登仙。……(《赤壁赋》)
大江东去,浪淘尽,千古风流人物……(《念奴娇赤壁怀古》)
这样的旷达,读来让人心胸为之开阔。这也大致代表了这位旷世奇才在人们心中的主要形象。
但我这次读其传记,对其第二次被贬谪后的诗文却尤其印象深刻。这一阶段的诗文少了些豪气,而更了些逸气。不仅行文自然巧妙,文本天成,少了些前一阶段的雕琢与修饰;而且思想上更加富于哲理与禅机,发人深省。东坡在给子侄的信中写道:“大凡为文,当使气象峥嵘,五色绚烂,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。”(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)如果说黄州时期的作品是“气象峥嵘,五色绚烂”,那么惠州儋州时期的作品则称得上“渐老渐熟,乃造平淡”了,这其实是文章的更高境。孙过庭论书道:“初学分布,但求平正;既知平正,务追险绝;既能险绝,复归平正。”学书如此,其实为文也这样,绚烂之后的平和冲淡,真正代表了人文俱老的最高境界。
来看看这一时期苏轼的处境和作品吧。
元祐八年(1093),苏轼,身至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,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下任宰相的最佳人选,正是“冠盖满京华”的时期。然而高太后去世,政坛巨变,于是绍圣元年(1094),苏轼千里迢迢奔赴贬所(英州),一路上朝廷五改谪命,最终贬到惠州。
此时的苏轼已是59岁的老人,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已于去年去世,身边只有小儿苏过,和侍妾朝云。白须潇散谪岭海之际,其心境可想而知,也正因此其诗文中流露出的哲思是那么真切动人。
贬往惠州路上,过大庾岭时,他写道:
一念失垢污,身心洞清净。
浩然天地间,惟我独也正。
今日岭上行,身世永相忘。
仙人抚我顶,结发受长生。
没有悲伤,没有哀怨,一切的辱与荣,垢与净,执迷与觉悟仿佛都在大庾岭上分开,此时的东坡居士已将过去的所有尘世染污抛下,等待的是仙人为之抚顶,助其修道成功。
于是经过曹溪南华寺时他写道:
我本修行人,三世积精练。中间一念失,受此百年谴。
他认为自己本事修行之人,只不过因中途一念之失,误落尘网中,遭受了这么多年的坎坷。可见此时的佛老思想成为了其意识的主导。
绍圣元年十月抵达惠州贬所时感叹道:
仿佛曾游岂梦中,欣然鸡犬识新丰。
这难道是梦中吗?我以前仿佛到过这个地方。这真是太富禅机了,《红楼梦》中的宝玉第一次见到林妹妹就说,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。正所谓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,宝玉之语和东坡之诗,真是灵性之人的睿智之语。
东坡惠州的诗文,正是借助佛老思想,取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脱:
譬如原是惠州秀才,累举不第,有何不可!(《与程正辅提刑》)
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,却在一个小村院子,折足铛中,罨糙米饭便吃,便过一生也得。(《与参寥书》)
此时的文章真的是妙手偶得,自然天成,臻于化境。随意的一篇游记,给人无限启迪:
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,纵步松风亭下。足力疲乏,思欲就亭止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,意谓是如何得到?良久,忽曰: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?”由是如挂钩之鱼,忽得解脱。若人悟此,虽兵阵相接,鼓声如雷霆,进则死敌,退则死法,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。(《记游松风亭》)
这已不是早期的五色绚烂,流光溢彩,思想上也不再有那么多的豪气与执念;而是一任天成,平和冲淡而哲思深宏。就连一次小小的搬家,随笔写来也能发人深省:
绍圣元年十月二日,轼始至惠州,寓居嘉佑寺松风亭。杖屦所及,鸡犬皆相识。明年三月,迁于合江之行馆。得江楼廓彻之观,而失幽深窈窕之趣,未见所欣戚也。岭南岭北,亦何异此?(《题嘉祐寺壁》)
他认为身处高位和谪居岭南就像搬家一样,一处有一处的妙处,一处有一处的局限,这样看来,便可随遇而安了。
果然,稍后来到“食无肉,病无药,居无室,出无友,冬无炭,夏无寒泉”的儋州,他也能怡然处之。此时,他已能够将老庄与佛家的思想出神入化的运用了,可谓用一生之浮沉阐释了释道之哲学:
始至南海,环视天水无际,凄然伤之曰:“何时得出此岛耶?”已而思之,天地在积水中,九州在大瀛海中,中国在少海中,有生孰不在岛者?覆盆水于地,芥浮于水,蚁附于芥,茫然不知所济。少焉水涸,蚁即径去。见其类,出涕曰:“几不复与子相见。”岂知俯仰之间,有方轨八达之路乎?念此可以一笑。
人生的局限无处无境不在,如此观之,一切便可释然了。这种文字置于《庄子》三十三篇中,也别无二致了。
谪居儋州之际,朝云已经去世,身边的亲人只有苏过一个,积蓄已基本花光,而自然环境险恶。而这位精神的富翁,却能用自己的达观,将如此贬谪之地,变为乐土。并写出《谪居三适》这样平易而富于哲思的诗作。
兹录其一:
旦起理发
安眠海自运,浩浩潮黄宫。
日出露未晞,郁郁蒙霜松。
老栉从我久,齿疏含清风。
一洗耳目明,习习万窍通。
少年苦嗜睡,朝谒常匆匆。
爬搔未云足,已困冠巾重。
何异服辕马,沙尘满风鬃。
琱鞍响珂月,实与杻械同。
解放不可期,枯柳岂易逢。
谁能书此乐,献与腰金翁。
早起梳头百下,是苏轼坚持一生的习惯,以此养生能“一洗耳目明,习习万窍通”。在这贫瘠险恶的海岛之上,如此平凡的生活细节竟成了丰厚的精神享受。此时的苏轼已经不是那个“纵一苇之所如,凌万顷之茫然”的东坡居士,而纯然是一位饱尝甘苦归于平和的老人,于日常细节中品出人生真谛。于是他感叹,年少时嗜睡,但为了上朝总不免匆匆早起,只能随便搔几下头发,还要佩戴重重的冠巾。现在想来与驾辕之马没什么不同,都是满头风尘,身上佩戴的玉饰发出的声音,实在和犯人身上刑具发出的声音一样。
至此,苏轼还是那个苏轼。但已从当年的豪放旷达,变为睿智通脱;由流光溢彩,变为平淡冲和;由辞采华茂,变为浑然天成了。(耿世涛)